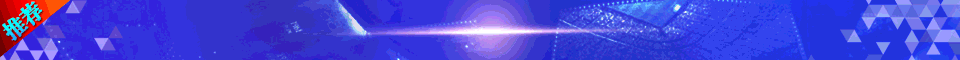- 收藏
- 返回
半生遗憾
祖屋的屋后,有条高水渠,曾经有水流过,现已无水流通,满生野草。
2005年的酷夏,我带我人生中的第二个女人回祖屋,看望老父母后,便领她至屋后的高渠散步,女人怕草中有蛇,撒娇着要回去,我说要寻些草药,叫她先回家。待她离开后,我沿着高渠溯走,扒开浓绿的野草,看不到蛇的踪影,却看到了渠水曾经流过的痕迹。
像所有的事物一样,高渠也有它辉煌的历史;二十年前,故乡肥沃的田野,都由高渠灌溉,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命脉。那年酷夏,高渠水断,我和两个夥伴往高渠玩耍,远远看见高渠里有两条赤裸的人体在纠缠,我们的头儿猪皮(花名)迅速趴倒,我和另一个夥伴甲鸟(花名)也跟着他趴地,他回头说,有好戏看,我们偷偷过去。
猪皮和甲鸟都是十六岁的少年,猪皮生得粗黑矮壮,甲鸟比猪皮高,没有猪皮的粗壮,因此甲鸟尊重猪皮的拳头,把一切的领导权交给猪皮;至于十三岁的我,是三人中最瘦弱的,自然是他们的小弟。几年之后,读到三国,我才发现,最弱的家夥是大哥,最强蛮的却是小弟,不胜唏嘘。
我们听从头儿的吩咐,沿着高渠垒边爬进,因高渠垒堤的野草和松木掩护,我们顺利靠近,三人趴在草丛中,偷偷地伸出脸去看,虽然远隔三十多米,但还是把在高渠杂草上纠缠的两个裸人看清楚了,却是村里著名的美女黄芙兰和才子李原持,我们三人你看我、我望你的干瞪眼一阵,趴在中间的猪皮,把他的臭嘴堵在我的耳朵,问我:「山猴,是你家隔壁的野妞,她真的干得出这种事!」芙兰被村人称为野妞,她生性好动,性格甚为叛逆,敢爱敢恨,谁把她惹急了,最粗野的话她都能骂出嘴,因她这种性格,惹得一些人憎恶,赠她「野妞」之浑号,又因她生得健康秀丽、青春明美,使得村里老老少少一堆男人做梦都想她……「猪皮,野妞的奶子真大,跟你家嫂子有得比!」甲鸟从草叶间缝中努力地窥望,屁股悄悄拱了起来,猪皮转眼看去,也跟着拱起屁股,我觉得奇怪,拍拍猪皮的屁股,他转首低骂:山猴,别拍,断了我的屌,我拆你的骨!
「甲鸟,我嫂子比野妞大,她喂奶的时候,托出那么一堆肉,就往孩子的小嘴塞。」甲鸟舔舔干燥的嘴唇,眼睛眨也不眨一下,说:猪皮,你嫂子的奶虽大,可没有野妞的好看,瞧那结实劲儿,圆圆胀胀,又白又嫩,粘鼠(李原持花名)的手抓上去,她的肉红扑红扑,惹得我口水都流了。
「那小子平时正正经经的,却在这种地方干这种缺德事。村里的人都说他是大学士,我呸!鸡巴毛的,蹶起屁股专找缝洞钻,啊我呸!野妞这贼婆娘,在我们面前装辣泼,在弱鸡巴面前扒开洞,我呸,比我们上月嫖的野鸡还要贱,啊我呸!」两人家里穷,早已辍学,平时在家务农,有时跟大人到县城做些苦力,用辛苦赚来的血汗钱,偷偷睡过野女人,回头揪出家夥向我炫耀,挥着拳头警告我不能告诉别人;我害怕他们的拳头,一直守口如瓶。
「小声些,他们听到……」
「啊我呸!」
猪皮虽然气恨,但不敢太大声,只因李原持的老子是村支书,这小官儿能够压死人,他猪皮拳头再粗、脑袋再浑,也不会傻得跟李支书的官威对抗,所以他继续拱着屁股瞅看。
当看到李原持扒开野妞的双腿、趴着吃她的黑毛的时候,两个家夥把手伸进裤裆扰动,如此一阵,猪皮干脆翻身倒躺,拉下裤头,抽出黑黑的、粗短的屌,不停地套弄,不停地低声咒骂:「啊我呸!狗娘养的粘鼠,操那么好的屄,老子把所有的钱砸了,只得操鸡婆的臭屄,啊我呸……」「猪皮,别吵,看粘鼠跟野妞的样,似乎是第一次,你瞧弄得的多揪人,粘鼠那物比你长、比我粗,可怎么也弄不进野妞的屄,野妞有些不耐烦。」「瞧!瞧个屁,先解决自己的问题,你娘的瞧着更揪人!我射泡家夥出来再陪你瞧……」「哇,野妞推开粘鼠了,猪皮,快瞧,野妞的毛好少,比我们玩的鸡婆的毛少多了。」猪皮翻身过来,瞪眼看去,见李原持扑到芙兰的身上,扛起她的双腿,蹶着屁股往她的黑毛插……「你快些,被人撞见,你我不用见人。你不是说你爸同意你娶我做媳妇吗?
为何不带我到你家,到了你家,我随你……」
「我急!明天要回省城读书,好久才回一趟,等完成学业,我就娶你……」「啊……我痛……」「进了,进了!」李原持兴奋地喝叫,猪皮和甲鸟也低声喊「进了」,仿佛他们的屌也插了进去,一股劲儿地跟着兴奋,然而李原持紧抽几下,趴倒在野妞丰满的肉体,呼啦啦的虚喘。
两人大感失望,像泄了气的气球软在草丛,猪皮控制不住情绪,喝骂:啊我呸!粘鼠大早泄,比甲鸟还软卵,啊我呸……「是谁?出来!」猪皮的「呸」被苟合的男女听到,李力持裸跑过来,我们躲之不及。
猪皮和甲鸟对望了一眼,抽起裤头钻出草木,迅速迎上李原持,猪皮挥拳把李原持打倒,甲鸟趁势冲到野妞身旁,把两人的衣服从野妞手中抢过,挥动着衣服,喊道:「粘鼠,向你老子告状啊,我们很怕你老子!」和猪皮扭打的李原持僵持当场,惊慌失撒地看着甲鸟,被猪皮揍了两拳,他犹然未觉。
「甲鸟,这小子阴险,让他恶人先告状,我们死得难看,你去把全村的人叫来,教他老子连官都当不成,看他如何嚣张!」「不……不要……是野妞勾引我……」「啊我呸!野妞勾引你?虽然我小你三年,但比你雄壮有力,怎么不见她勾引我?」「真的,是她勾引我的!她骚得很,看见男人就勾引,不信你们试试,她很骚!」「我先试……」离野妞最近的甲鸟丢掉衣服,扑到羞怒的野羞身上,压着她乱吻,我看见他脱掉裤子,抽出他白净的屌插进野妞的双腿处,于是听到野妞低声的哭骂:「狗娘养的,你们这群狗娘养的,老娘做鬼也饶不了你们!」我已经吓得哭了,裤裆灌满了尿,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,冲过去推开甲鸟,哭喊:「你们不能这样,她都哭了,她平时对我很好……」「滚一边撒尿去!」甲鸟扯住我的头发,把我丢到一边,扑到芙兰身上,给了她两个耳光,扛起她的双腿,长屌插进她流血的肉洞,痛得她阵阵哭骂,我爬过去要推他,他挥手打在我的脸,我跌到一边,看见他猛插一阵,抽出染血的长屌,几滴精液从他的龟头滑落……「大爽,好紧的小屄!」「啊我呸!我也来一炮!」
猪皮冲过来,脱掉裤子,扛起芙兰的双腿,粗壮的短屌插入鲜红的穴,把两片嫩的肉抽拉得隆翻,她发出撕心裂肺的哭骂,双眼却看着李原持,但见李原持裸身走近,取了他的衣服急急穿上,话也不说一句就逃离。
她双眼一闭,泪水独悲流。
「猪皮,你放过野妞吧,她快死了!」
「啊我呸!」猪皮一阵猛插,射了精,站起来把我提起,粗拳轰在我的小腹上,「山猴,今日之事,你敢泄露半句,我砸碎你的头!」「猪皮,把山猴的裤子脱掉,让他的小屌也干一炮,他就不敢说了。」「啊我呸!甲鸟你的脑子真好使……」猪皮脱掉了我的裤子,看到我的小屌软软,他和甲鸟愣了一下,他抓着我的小屌套弄、拍打,但不知为何,我的小鸟始终振飞不起,他又在我的小腹轰打一拳,骂说:「这小子性无能,没种的家夥,只会窝在裤裆撒尿,啊我呸,倒霉!
甲鸟,我们速闪……」
两人抓起衣服就跑,剩下我和芙兰,我偷偷地看她,她也在看我,原本充满青春野性的眼眸,此时涣散无光,只余眼泪和茫然。
对望许久,她颤动了几下嘴唇,无力地说:「山浩,过来,姐姐抱抱……」我犹豫片刻,小心地爬到她身旁,她抱我过去,紧紧勒住我的身体,虽然我已经十三岁,可是我的身体还没有开始发育,比她矮半个头;但她其实也不高,只有一百五十八公分。
她把我的脸压在她的乳峰,她是健康的农村女孩,勤劳的天性令她的肉体结实,耸圆的双峰压得我喘不过气,我使劲地推她的胸,她终于放开我,抱着我没头没脑地乱亲。
我真的很不习惯,挣扎着退离她的怀抱,看到泪流满面的她,不忍心看,低眼又看到她张开的双腿,却见那黑的毛生在她的阴阜之上,只是小小的一撮,底下的大阴唇生着稀疏的淡阴毛,看似没生一般,洁白的阴唇有些擦红,稍稍张开的阴缝里面是粉红的嫩肉,不知是谁的精液从里面一点一点的流出……「山浩,想插吗?姐姐陪你!」她作贱地问我。
我猛摇小脑袋,说:「你流血了。」
「哇!」她伸手又抱我,嘶声大哭,「姐姐遇到了畜生和禽兽,山浩不懂,姐姐这辈子毁了。早知山浩疼姐姐,姐姐等山浩长大……姐姐下辈子找山浩!」我不是很明白她在说什么,但她推开了我,裸着身体冲上渠堤,往堤坝的松木撞去,我惊怕得大喊:「野妞,我插你!」她的双腿一软,倒坐在松树旁,回首看我,见我捏着软软的小屌朝她走来,她又是哭又是笑,我跪到她面前,学着扛起她的双腿,软屌儿往她的小红洞塞,却怎么也进不了,她痴痴地哭笑,任我弄着,许久,她问:「山浩,为啥要插姐姐?」「——我不插你,你要撞树;我插了你,你就不撞。」「山浩,知道姐姐以后都嫁不到好人了么?」「姐姐一定要嫁人?」「嗯,女人都得嫁……」
「我是好人吗?」
「嗯,山浩是好人,以后长大也还要做好人,知道么?」「野妞,你嫁给我吧,我也是好人了,你能嫁给好人。」「嗯,姐姐现在就嫁给你,山浩是好男人,不是没种的男人……」她推我倒地,伏在我的胯,手指捏我的小软屌,张嘴吞含,她嘴嫩嫩滑滑、温暖又润湿,我只是感觉舒服,渐渐感到下体有些发热,小屌像是在胀尿,我急了,仰身起来推她的脸,说:「野妞,我要撒尿。」「山浩果然不是没种的男人。」她坐直身体,说。
我坐起来低头看,只见我的小屌硬直,嫩嫩白白的一条,没有猪皮的粗大,但也有了他的长度,红红嫩嫩的半个龟头露出,我傻傻地看着,喃喃自语:「以前我也硬,为什么刚才不硬?」「因为山浩刚才心疼姐姐,所以不会硬,现在山浩硬了,趁着姐姐的鲜血未停,山浩也插进来吧,姐姐以后再也不能为山浩流血了。」她说着,靠着松树,曲张双腿,等待我的插入。
我迟迟地没有动作,她又说:「山浩,是不是嫌姐姐脏?」「——野妞不脏,野妞白白。」「你插进来,姐会白白……」「野妞会哭……」
「姐姐不哭,山浩插进来,姐姐都不哭!」
她伸手过来,捏着我的屌根,拉到她的鲜红的小缝洞,触到她的肉的刹那,嫩龟头酥痒,我打了个颤,她把我的龟头挤入她的肉缝,暖暖的、湿湿的,很紧很舒服,我自然而然地插进去,紧紧的感觉中夹着擦热的疼痛,我叫喊一声,抽出嫩屌,看见原本裹着半个龟头的包皮被拉扯得很上,嫩红的龟头整个露出。
疼痛来自龟头底下,我轻轻翻转小屌,一看包皮系带断了,正在流血,我慌了,哭叫:「野妞,我流血了,好痛……」「让姐姐看看!」她温柔地捏住我的屌根,把龟头翻仰,看见流血,她也愣了一下,接着给我呵吹。
「都是姐姐害了山浩!等山浩伤好,姐姐再给山浩插,山浩什么时候想插姐姐就什么时候插!姐姐高兴哩,山浩给姐姐流了血,姐姐是山浩的第一个女人,瞧山浩现在的嫩小鸡,以后长大,会变成粗粗壮壮的铁公鸡,姐姐的小洞都不知道能不能装得下。」「那我不要长大——」「傻瓜,男人一定要长大,越大越好……」
「野妞喜欢大大的吗?猪皮他的很大……」
「姐姐只喜欢山浩你,山浩以后会比猪皮大比甲鸟长……」「我不要那么长那么大,野妞会痛。」「姐姐不怕,姐姐能够装下山浩的一切……」「野妞,你干的好事!」
*** *** *** ***
我们没想到那时会有人找来,更没想到来的是野妞的父母和我的爸妈,后来我们才知道,猪皮和甲鸟回去之后找到我们的家长,说野妞勾引我在高渠苟合,因为我的年龄和身体都小,两家都把这事怪到野妞头上,但两家都不敢声张,猪皮、甲鸟和粘鼠更是不敢声张,这事便在悄无声息中过去。
野妞的父母觉得愧对我的爸妈,我爸妈也不肯原谅野妞,两家的关系变得生陌,直至四个月后,野妞的肚子大起来,她的父母迫于形势,逼她嫁给本村的四十岁的光棍李贵。
我被爸妈丢到县城的舅舅家读书,三年来不准回家,我舅也从不向我说我家的事情,因此对野妞的命运一概不知。初中毕业后,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县城重点高中,高一结束的那个暑假,爸妈方肯领我回家,其时我已经十七岁,生得只有一百七十三公分,虽然不是很高大,但比当年的猪皮、甲鸟都高壮。
野妞在四年后再次见到我的时候,她愣是傻笑,笑了很久,笑得眼泪稀哩地流,她身旁的美丽小女孩扯着她的衣袖,说:「妈妈,你又哭了。」「你变了!」我不敢跟她多说,急急忙忙地逃开,她在我背后大哭,她的女儿也跟着哭。
我不敢问爸妈有关她的事情,但是奇怪她为何会住在娘家,于是通过一些旁言,我了解到李贵在她的女儿出生后的第九个月,不知怎么的,和猪皮厮打,被猪皮捞起石块砸碎脑袋,结果猪皮最终没有用石头砸破我的头,反而被一颗小小的子弹崩开了他的脑壳。
李贵死了,他光棍一条,没亲没故,野妞带着九个月的女儿回到娘家……*** *** *** ***回家后的第六天,野妞的父母来找我,我不知道他们的来意,但感无脸面对他们,或者他们也同样感到无脸面对我,他的父亲不停地抽着水烟,她的母亲也不言不语,我只得问他们找我有什么事,她的母亲忽然朝我下跪,哭着说对不起我,她的父亲吐出一口浓烟,说:「你陪陪野妞吧……她苦,常流泪,自从你回来,她没日没夜地哭,动不动就揪打女儿,是我们对不起你们,我们有罪啊!」正感不知所措,我爸妈出现在门前,爸说:「你也长大了……你喜欢,就去吧。」……我冲进野妞的房,看见她坐在床沿,抚摸熟睡的女儿,并不像她父母所说的暴力,而是满怀母性的温柔。
她看见我,流了一会泪,哽咽:「你来了?」
「我来了。」我说。我把门反锁了。
「我以为你不要姐姐了。」她说。她哭,她也笑。
她解衣。两颗乳房露出,也露出了她满身的伤痕,看得我心酸。
乳房比四年前大很多,像木瓜,比木瓜圆,但没有垂吊,它们耸挺。
我双手托她的肉,弯腰含她的奶,她抱着我的头,说你要吃奶不,弄大姐姐的肚子,姐姐天天喂你奶吃。我说我要吃你。我双手扒脱掉她的裤,她张着腿,一双小腿儿吊在床前,黑浓的阴毛把她的阴户遮盖。我说你浓了,她说久未被人耕种的地,自然生满野草。
她又说让我瞧瞧你的锄柄……
我站直身体,解开裤头,肉屌跳出,她双手紧握我的屌,说,我的山浩果然没辜负姐姐的期望,生得一根好屌,又粗又长,红通通的像要喷血……她张嘴把我的屌吞吮,我愣然片刻,双手抓住她的豪乳揉搓,眼睛却看着她的脸庞,其实她并没有变多少,只是比以前多了妇女的神韵,也许因为劳作,她脸上的肌肤透着红黑,略见粗糙,但那秀美的脸蛋依然保持当年的丰姿,我这时想起,她今年二十岁,而我之前把她当成妇女——二十岁,不就是一个青春少女么?
长期包裹在粗布里的肌肤洁白滑嫩,只是小腹有一些隆胀,但仍然结实和弹性,只是她的手掌,已经没有当年的细腻,握在我的肉屌上,她的手掌显得些许的粗糙、些许的过大……我没能够坚持多久,大概两分钟,急急地射精进她的嘴,她把精液吞了,仰脸朝我笑,说浓浓的热精她好喜欢,我埋首吻她的嘴,同样地品尝到我的精液的味道。
激吻后,她说,山浩,你吻吻姐姐的穴,姐姐曾干净十六年,被三个畜生弄脏,姐姐现在也干净了三年,但姐姐喜欢你再次把它弄脏,永远地把它弄脏……我跪在床前,扒开她的腿,双手拔开她黑浓的毛,看见她的屄,熟悉而又陌生,她本来洁白的阴唇变得有些深色,我记得以前她的阴唇也没有这么肥大,但现在肥隆起来,那道肉缝也稍稍地翻张,只有小阴唇依然桃红,由小阴唇组成的洞也比以前大了些,淫水从她的洞流出,湿红的小阴唇像被雨淋过的桃肉。
「山浩,是不是比以前难看?我生了孩子,缝了好几针……」我的脸钻进她的胯,咬住她的肉,她呻吟一声,没有继续说。
因为没洗澡的缘故,她的屄有点汗骚味,但不知道怎的,我喜欢这味儿,口舌捣着她的嫩肉,不停吮吸她的骚水。我的肉屌再次勃硬,她抱着我的头,说山浩插姐姐,山浩快插姐姐!
我扛起她的比以前粗圆的腿,发觉她的屁股比以前圆大、比以前更有肉感,我学着以前的样子,把肉屌抵插她的肉缝,努力了几下,未能进入,她咯咯地笑了,伸手抓住我的肉屌,往她的肉洞塞,整个龟头被她塞进肉穴,跟以前一样的紧,但这次我没有流血,她也没有。
她说我的肉屌让她好舒服,要我狠狠往里插,我使劲地沈腰刺插,肉屌整根插入她的肉洞,胀得她的大阴唇高高折隆,难以说出的舒服包围我的屌,人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插进女人的肉里的美好。
「山浩真好!山浩真强壮,山浩满足姐姐哩……」她哭,眼泪流得比骚水急。
「——你以前不是说,我插你的时候,你都不哭吗?」她说不哭,她喜欢;后来她又说,山浩插姐姐,姐姐就哭,天天给山浩哭,因为喜欢。
我说野妞,你的伤是谁打的。她说一个死鬼打的,她不从他,他揪着她在床打、绑着她打,打了又插、插了又打,她希望能够把肚里的野种打掉,可是野种没打掉,他倒被别人打死。我知道她说的死鬼是光棍李贵,不知该说什么,只是摸着她的伤痕,想哭,但哭不出。
她的屄水流得浓。我扛着她的腿,压在她的身,卖劲地插着,这次我插得很久,也许是刚射了精的缘故。她被我插得高兴,她说她高兴会流泪,不高兴也会流泪,她说她以前不流泪。
我没有语言,只有动作。我的动作只有一个,只是不停地插;插着她的肉。
她的肉柔软、多汁!我说野妞你松了,她说没松,水多了自然叫山浩插得顺畅。
她又说,你强奸我吧,下次你强奸我,我不给你流水,紧你!
我感动,说野妞都紧,她哭着说山浩也粗大。我喜欢她说我大屌,卖劲的插着。
我的汗水滴落她的身体,和她的汗水融合,她喘着说做完要和我洗鸳鸯浴,忽然推了我一把,翻身趴在床,嚷着狗插狗插山浩我要狗插,扯着我的屌要我做她的狗,我于是真做了她的公狗,但公狗不好做,我抓着她的奶水咬着她的背,没多少下就软了,屌吐白沫地趴在她的背上喘风。
她软在床,旁边躺着她的女儿。她伸手扯掉女儿的小裤,我看见她女儿的小缝,红嫩红嫩的可爱。她指着女儿的细缝,说山浩舔舔。我惊了,我不干。
她哭了,重复地要我吻她的女儿。我就看着女孩的小器,心里有种变态的冲动。我舔了,舔着女孩的嫩。
「什么感觉?」她问,我说:「咸。」
她咯咯地笑,「等野种长大,山浩把野种开了。」我惊觉她病态,但看起来不像疯。
此时女孩醒了,女孩哭,她揪起女儿的小白屁股,大巴掌地拍打,我抓住她的手。外面传来她父亲的声音,女孩哭得厉害,她父亲要进来,她扯了被单往身上盖,我裸着身把门打开,她父亲进来抱了她的女儿。他看了看我,朝我竖起个大拇指,啥也不说就出去了。
我回头,问她为何总要打女儿。她笑,笑得像哭。我抱了她。我的屌又硬,插进她的肉,有些干,很紧。
「山浩你可知道,我爹娘和你爸妈初时以为野种是你的,都不准我打。一年前我哥从外地回来,我打野种,他揪着我的头发打我,我把被三个畜生轮奸的事说了,他跑去打甲鸟,打断了甲鸟一条腿,他也蹲牢去了。」难怪我这趟回来没有见到她哥;记得当年发生那事,他哥觉得丢脸,什么都不说,跑到外面谋活事,因此野妞嫁的时候,她哥也不知晓。
说到她哥,她更是哭。她说她葬送了哥哥的幸福,她哥在外地几年,混了个名堂,拿了叠叠钞票回来给爹娘,只是赚到的钞票还没讨个媳妇,就为了她去蹲牢,她心里痛恨!
「过几年会出来。」我安慰她,吻她的汗和泪,也吃她的骚水。
我和她直到做天黑,她说她从未得到过这么多高潮。
吃了晚饭,她洗了澡又过来找我,我爸妈看见也没说什么。我抱了她到我的房,在床上滚到天亮,流了满床的水,但这次没了她的泪,只有汗和骚。
整晚,她不停地重复一句话:你肏我到死,我是你的肉,你肏我到死……*** *** *** ***整个暑假,我和野妞几乎都在床上渡过,这是我们两家的秘密,除了两家的父母,谁都不知道此事。然而不好的事情发生了,野妞的月事没来,在将要开学前的四天,我特意跑到县城给野妞买了验孕试纸,回来往她的尿里一插,她果然怀了我的种。
我把这事跟爸妈说了,爸妈和野妞的父母商量,野妞的父亲说生吧也给山浩生个孩子,不管别人怎么说。我爸妈也同意了,野妞那么喜欢我,是该有个我的孩子。
然而野妞似乎不高兴,我插她的肉的时候,问她不想替我生孩子吗,她说她是寡妇,我说不上学了跟她结婚。她苦笑,还是笑得咯咯地响,咬着我的鼻尖骂我浑,我说我真的娶。
「——我生是你的肉,死是你的魂,你以后有出息娶了媳,你回来看看我,理理我垄上的草。」我抽出肉屌,趴到她的屄,用牙齿梳理她的毛,说我这辈子只理你的草,她不愿意,说男人的耙要多理几块田的草,男人才会更有劲,还说她要把她田里的草理光了逼我去理别的田的草。我取了剪刀和剃胡的刀片,把她的毛剃光。
光洁的屄、隆起的肉、夹露的唇。我一把插了进去,她推开我,拿了工具把我的毛也剃掉,然后咯咯地笑,说进来,光头小弟进姐姐没有草的洞。我插了进去,没了毛的屄垄,像小女孩的肌肤一般嫩滑。
她说明天你陪我到集市吧,这辈子你还没有陪我到集市买过东西。天明我陪她到集市,但她没有买东西送我,买了一包不知名的药和一瓶酒又买了一把短刀和一叠冥钱,我问她为什么,她说我哪天不要她了,她就杀了我,顺便给我烧些纸钱。
虽然我很想相信她说的话是假的,但我的心还是感到寒。
回家和她做爱的时候,老想着她买的那把刀,扎在心里冰寒冰寒的……后天我要到县城上学,我有许多想要跟她说,她却不肯跟我说话,只是跟我死活地做。半夜里,她穿了短裤跑出去,回来时手里拿一瓶花生油,我问她做什么,她说如果不嫌脏,把最后的洞也给我。
我把花生油涂进她的屁眼,艰难地插入她的肛门,在干涩和油粘中,我很快射了精。
斑斑黄白和缕缕鲜血凝结在她油滑的屁眼,忘了擦……*** *** *** ***翌日,我忙碌着上学前的事项,整日没找野妞,也没见她出现,晚上找她的时候,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,问她的父母,他们也是不知。直到晚上九时多,有人冲至她家,说野妞杀人了,野妞杀了甲鸟……我们两家人往甲鸟家奔,十分钟后到达甲鸟的家门,见到门前堵着一堆人,甲鸟的老母哭得猪叫般的惨痛,他的两个兄弟也嚎叫不止。我推开人群,冲至门前,被他的两个兄弟拦住,我挥拳把他们打倒,冲进屋里,看见野妞赤裸地靠坐在床栏,胸前插着她那天买来的刀。
她看见我,还是咯咯地笑。
甲鸟的尸体,胯间一片惨红,他的屌被砍成好几断,丢弃在他的尸体旁……我喝喊:「你疯了?」「我是疯了,我早就疯了!我被三个畜生轮奸,胀了肚子,被逼嫁给光棍,天天被打……我故意跟猪皮偷奸,故意让光棍看到,叫他们狗咬狗,葬了他们的命。」「我今晚拿了酒,酒里掺着老鼠药,跟这拐子说要跟他续前缘,他爬上了我的肉,高兴地插我,高兴地喝了我的酒,我趁着他高兴得晕了,也高兴地取出藏在衣服的刀,高兴地捅他,他高兴地死了,我再高兴地把他的高兴也割去,然后他们来了,我要让他们知道老娘今晚有多高兴,于是高兴地插进自己的胸膛,老娘就是高兴!」「——你真的疯了!」我悲喝着,走向床前。
她甩手把刀抽出,血液喷涌……
我抢过她的刀,她哭,她说你痛吗,你痛的话怎么不见你流血?
血……
我把刀插进自己的大腿,横抱起她,一拐一拐地走出去。
没有人拦我,甲鸟的兄弟也让出了道……
我抱着虚弱的她,走进黑夜,她的父母和我的爸妈跟在后面。
「——山浩,我下辈子不要做野妞,我要做你温柔的姐姐,下辈子你认得我的肉吗?」「野妞的肉,我都认得……」「山浩,姐姐的肉今晚又脏了,以后都不能为你洗干净,但我留了一个干净的肉给你,她没有姓,只有名字,叫芙蓉……那肉虽然来得肮脏,但她本身很干净,你替我照顾好她,因为她也是姐姐的肉。」「嗯,我会照顾好芙蓉……」「山浩,姐姐还有个好恨的人,姐姐恨不得吃他的肉,可是他的肉是世界上最脏的,姐姐啃不下,你长大后找到他,看看他有没有女儿,然后你像他当年对待我一样,也把她的女儿糟蹋。」我没有说话,她逼着我回答,我只得点点头,在黑夜里,也不知道她是否看得清楚?
她说话的力气越来越弱,但是她似乎还有说不完的话要对我说,我只能够听着,什么话都说不上。
「山浩,我这辈子被葬了,同时我也葬了很多人。我葬了你的童真、葬了父母的脸面、葬了孩子的人生!但我,葬你在我的心里,从你说我哭的那刻起,姐姐就葬你在心里,葬得很深,谁都挖不起。」「我不知道你被我葬得可高兴,可是姐姐知道明天会被你亲手埋葬,姐姐真的好高兴!能够给山浩葬,是姐姐最幸福的时刻,所以姐姐提前买了纸钱,让山浩一路地撒,也让纸钱擦干姐姐一路的眼泪,因为姐姐怕太高兴,流太多的泪!
山浩,你叫一声姐姐,你一直都没叫过……」
「姐。」我哭。
「别哭!山浩,姐姐给你唱首歌儿,姐姐今晚高兴,把藏在心里四年的歌儿唱给你听:
小小的鸟儿,跳啊跳
跳上了竹叶梢;
轻轻的风儿,摇啊摇
摇落了一地愁。
摇啊摇,女儿笑!
笑落泪水,满地浇。
葬我的眼泪,
在你心里头……」
*** *** *** ***
【完】
2005年的酷夏,我带我人生中的第二个女人回祖屋,看望老父母后,便领她至屋后的高渠散步,女人怕草中有蛇,撒娇着要回去,我说要寻些草药,叫她先回家。待她离开后,我沿着高渠溯走,扒开浓绿的野草,看不到蛇的踪影,却看到了渠水曾经流过的痕迹。
像所有的事物一样,高渠也有它辉煌的历史;二十年前,故乡肥沃的田野,都由高渠灌溉,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命脉。那年酷夏,高渠水断,我和两个夥伴往高渠玩耍,远远看见高渠里有两条赤裸的人体在纠缠,我们的头儿猪皮(花名)迅速趴倒,我和另一个夥伴甲鸟(花名)也跟着他趴地,他回头说,有好戏看,我们偷偷过去。
猪皮和甲鸟都是十六岁的少年,猪皮生得粗黑矮壮,甲鸟比猪皮高,没有猪皮的粗壮,因此甲鸟尊重猪皮的拳头,把一切的领导权交给猪皮;至于十三岁的我,是三人中最瘦弱的,自然是他们的小弟。几年之后,读到三国,我才发现,最弱的家夥是大哥,最强蛮的却是小弟,不胜唏嘘。
我们听从头儿的吩咐,沿着高渠垒边爬进,因高渠垒堤的野草和松木掩护,我们顺利靠近,三人趴在草丛中,偷偷地伸出脸去看,虽然远隔三十多米,但还是把在高渠杂草上纠缠的两个裸人看清楚了,却是村里著名的美女黄芙兰和才子李原持,我们三人你看我、我望你的干瞪眼一阵,趴在中间的猪皮,把他的臭嘴堵在我的耳朵,问我:「山猴,是你家隔壁的野妞,她真的干得出这种事!」芙兰被村人称为野妞,她生性好动,性格甚为叛逆,敢爱敢恨,谁把她惹急了,最粗野的话她都能骂出嘴,因她这种性格,惹得一些人憎恶,赠她「野妞」之浑号,又因她生得健康秀丽、青春明美,使得村里老老少少一堆男人做梦都想她……「猪皮,野妞的奶子真大,跟你家嫂子有得比!」甲鸟从草叶间缝中努力地窥望,屁股悄悄拱了起来,猪皮转眼看去,也跟着拱起屁股,我觉得奇怪,拍拍猪皮的屁股,他转首低骂:山猴,别拍,断了我的屌,我拆你的骨!
「甲鸟,我嫂子比野妞大,她喂奶的时候,托出那么一堆肉,就往孩子的小嘴塞。」甲鸟舔舔干燥的嘴唇,眼睛眨也不眨一下,说:猪皮,你嫂子的奶虽大,可没有野妞的好看,瞧那结实劲儿,圆圆胀胀,又白又嫩,粘鼠(李原持花名)的手抓上去,她的肉红扑红扑,惹得我口水都流了。
「那小子平时正正经经的,却在这种地方干这种缺德事。村里的人都说他是大学士,我呸!鸡巴毛的,蹶起屁股专找缝洞钻,啊我呸!野妞这贼婆娘,在我们面前装辣泼,在弱鸡巴面前扒开洞,我呸,比我们上月嫖的野鸡还要贱,啊我呸!」两人家里穷,早已辍学,平时在家务农,有时跟大人到县城做些苦力,用辛苦赚来的血汗钱,偷偷睡过野女人,回头揪出家夥向我炫耀,挥着拳头警告我不能告诉别人;我害怕他们的拳头,一直守口如瓶。
「小声些,他们听到……」
「啊我呸!」
猪皮虽然气恨,但不敢太大声,只因李原持的老子是村支书,这小官儿能够压死人,他猪皮拳头再粗、脑袋再浑,也不会傻得跟李支书的官威对抗,所以他继续拱着屁股瞅看。
当看到李原持扒开野妞的双腿、趴着吃她的黑毛的时候,两个家夥把手伸进裤裆扰动,如此一阵,猪皮干脆翻身倒躺,拉下裤头,抽出黑黑的、粗短的屌,不停地套弄,不停地低声咒骂:「啊我呸!狗娘养的粘鼠,操那么好的屄,老子把所有的钱砸了,只得操鸡婆的臭屄,啊我呸……」「猪皮,别吵,看粘鼠跟野妞的样,似乎是第一次,你瞧弄得的多揪人,粘鼠那物比你长、比我粗,可怎么也弄不进野妞的屄,野妞有些不耐烦。」「瞧!瞧个屁,先解决自己的问题,你娘的瞧着更揪人!我射泡家夥出来再陪你瞧……」「哇,野妞推开粘鼠了,猪皮,快瞧,野妞的毛好少,比我们玩的鸡婆的毛少多了。」猪皮翻身过来,瞪眼看去,见李原持扑到芙兰的身上,扛起她的双腿,蹶着屁股往她的黑毛插……「你快些,被人撞见,你我不用见人。你不是说你爸同意你娶我做媳妇吗?
为何不带我到你家,到了你家,我随你……」
「我急!明天要回省城读书,好久才回一趟,等完成学业,我就娶你……」「啊……我痛……」「进了,进了!」李原持兴奋地喝叫,猪皮和甲鸟也低声喊「进了」,仿佛他们的屌也插了进去,一股劲儿地跟着兴奋,然而李原持紧抽几下,趴倒在野妞丰满的肉体,呼啦啦的虚喘。
两人大感失望,像泄了气的气球软在草丛,猪皮控制不住情绪,喝骂:啊我呸!粘鼠大早泄,比甲鸟还软卵,啊我呸……「是谁?出来!」猪皮的「呸」被苟合的男女听到,李力持裸跑过来,我们躲之不及。
猪皮和甲鸟对望了一眼,抽起裤头钻出草木,迅速迎上李原持,猪皮挥拳把李原持打倒,甲鸟趁势冲到野妞身旁,把两人的衣服从野妞手中抢过,挥动着衣服,喊道:「粘鼠,向你老子告状啊,我们很怕你老子!」和猪皮扭打的李原持僵持当场,惊慌失撒地看着甲鸟,被猪皮揍了两拳,他犹然未觉。
「甲鸟,这小子阴险,让他恶人先告状,我们死得难看,你去把全村的人叫来,教他老子连官都当不成,看他如何嚣张!」「不……不要……是野妞勾引我……」「啊我呸!野妞勾引你?虽然我小你三年,但比你雄壮有力,怎么不见她勾引我?」「真的,是她勾引我的!她骚得很,看见男人就勾引,不信你们试试,她很骚!」「我先试……」离野妞最近的甲鸟丢掉衣服,扑到羞怒的野羞身上,压着她乱吻,我看见他脱掉裤子,抽出他白净的屌插进野妞的双腿处,于是听到野妞低声的哭骂:「狗娘养的,你们这群狗娘养的,老娘做鬼也饶不了你们!」我已经吓得哭了,裤裆灌满了尿,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,冲过去推开甲鸟,哭喊:「你们不能这样,她都哭了,她平时对我很好……」「滚一边撒尿去!」甲鸟扯住我的头发,把我丢到一边,扑到芙兰身上,给了她两个耳光,扛起她的双腿,长屌插进她流血的肉洞,痛得她阵阵哭骂,我爬过去要推他,他挥手打在我的脸,我跌到一边,看见他猛插一阵,抽出染血的长屌,几滴精液从他的龟头滑落……「大爽,好紧的小屄!」「啊我呸!我也来一炮!」
猪皮冲过来,脱掉裤子,扛起芙兰的双腿,粗壮的短屌插入鲜红的穴,把两片嫩的肉抽拉得隆翻,她发出撕心裂肺的哭骂,双眼却看着李原持,但见李原持裸身走近,取了他的衣服急急穿上,话也不说一句就逃离。
她双眼一闭,泪水独悲流。
「猪皮,你放过野妞吧,她快死了!」
「啊我呸!」猪皮一阵猛插,射了精,站起来把我提起,粗拳轰在我的小腹上,「山猴,今日之事,你敢泄露半句,我砸碎你的头!」「猪皮,把山猴的裤子脱掉,让他的小屌也干一炮,他就不敢说了。」「啊我呸!甲鸟你的脑子真好使……」猪皮脱掉了我的裤子,看到我的小屌软软,他和甲鸟愣了一下,他抓着我的小屌套弄、拍打,但不知为何,我的小鸟始终振飞不起,他又在我的小腹轰打一拳,骂说:「这小子性无能,没种的家夥,只会窝在裤裆撒尿,啊我呸,倒霉!
甲鸟,我们速闪……」
两人抓起衣服就跑,剩下我和芙兰,我偷偷地看她,她也在看我,原本充满青春野性的眼眸,此时涣散无光,只余眼泪和茫然。
对望许久,她颤动了几下嘴唇,无力地说:「山浩,过来,姐姐抱抱……」我犹豫片刻,小心地爬到她身旁,她抱我过去,紧紧勒住我的身体,虽然我已经十三岁,可是我的身体还没有开始发育,比她矮半个头;但她其实也不高,只有一百五十八公分。
她把我的脸压在她的乳峰,她是健康的农村女孩,勤劳的天性令她的肉体结实,耸圆的双峰压得我喘不过气,我使劲地推她的胸,她终于放开我,抱着我没头没脑地乱亲。
我真的很不习惯,挣扎着退离她的怀抱,看到泪流满面的她,不忍心看,低眼又看到她张开的双腿,却见那黑的毛生在她的阴阜之上,只是小小的一撮,底下的大阴唇生着稀疏的淡阴毛,看似没生一般,洁白的阴唇有些擦红,稍稍张开的阴缝里面是粉红的嫩肉,不知是谁的精液从里面一点一点的流出……「山浩,想插吗?姐姐陪你!」她作贱地问我。
我猛摇小脑袋,说:「你流血了。」
「哇!」她伸手又抱我,嘶声大哭,「姐姐遇到了畜生和禽兽,山浩不懂,姐姐这辈子毁了。早知山浩疼姐姐,姐姐等山浩长大……姐姐下辈子找山浩!」我不是很明白她在说什么,但她推开了我,裸着身体冲上渠堤,往堤坝的松木撞去,我惊怕得大喊:「野妞,我插你!」她的双腿一软,倒坐在松树旁,回首看我,见我捏着软软的小屌朝她走来,她又是哭又是笑,我跪到她面前,学着扛起她的双腿,软屌儿往她的小红洞塞,却怎么也进不了,她痴痴地哭笑,任我弄着,许久,她问:「山浩,为啥要插姐姐?」「——我不插你,你要撞树;我插了你,你就不撞。」「山浩,知道姐姐以后都嫁不到好人了么?」「姐姐一定要嫁人?」「嗯,女人都得嫁……」
「我是好人吗?」
「嗯,山浩是好人,以后长大也还要做好人,知道么?」「野妞,你嫁给我吧,我也是好人了,你能嫁给好人。」「嗯,姐姐现在就嫁给你,山浩是好男人,不是没种的男人……」她推我倒地,伏在我的胯,手指捏我的小软屌,张嘴吞含,她嘴嫩嫩滑滑、温暖又润湿,我只是感觉舒服,渐渐感到下体有些发热,小屌像是在胀尿,我急了,仰身起来推她的脸,说:「野妞,我要撒尿。」「山浩果然不是没种的男人。」她坐直身体,说。
我坐起来低头看,只见我的小屌硬直,嫩嫩白白的一条,没有猪皮的粗大,但也有了他的长度,红红嫩嫩的半个龟头露出,我傻傻地看着,喃喃自语:「以前我也硬,为什么刚才不硬?」「因为山浩刚才心疼姐姐,所以不会硬,现在山浩硬了,趁着姐姐的鲜血未停,山浩也插进来吧,姐姐以后再也不能为山浩流血了。」她说着,靠着松树,曲张双腿,等待我的插入。
我迟迟地没有动作,她又说:「山浩,是不是嫌姐姐脏?」「——野妞不脏,野妞白白。」「你插进来,姐会白白……」「野妞会哭……」
「姐姐不哭,山浩插进来,姐姐都不哭!」
她伸手过来,捏着我的屌根,拉到她的鲜红的小缝洞,触到她的肉的刹那,嫩龟头酥痒,我打了个颤,她把我的龟头挤入她的肉缝,暖暖的、湿湿的,很紧很舒服,我自然而然地插进去,紧紧的感觉中夹着擦热的疼痛,我叫喊一声,抽出嫩屌,看见原本裹着半个龟头的包皮被拉扯得很上,嫩红的龟头整个露出。
疼痛来自龟头底下,我轻轻翻转小屌,一看包皮系带断了,正在流血,我慌了,哭叫:「野妞,我流血了,好痛……」「让姐姐看看!」她温柔地捏住我的屌根,把龟头翻仰,看见流血,她也愣了一下,接着给我呵吹。
「都是姐姐害了山浩!等山浩伤好,姐姐再给山浩插,山浩什么时候想插姐姐就什么时候插!姐姐高兴哩,山浩给姐姐流了血,姐姐是山浩的第一个女人,瞧山浩现在的嫩小鸡,以后长大,会变成粗粗壮壮的铁公鸡,姐姐的小洞都不知道能不能装得下。」「那我不要长大——」「傻瓜,男人一定要长大,越大越好……」
「野妞喜欢大大的吗?猪皮他的很大……」
「姐姐只喜欢山浩你,山浩以后会比猪皮大比甲鸟长……」「我不要那么长那么大,野妞会痛。」「姐姐不怕,姐姐能够装下山浩的一切……」「野妞,你干的好事!」
*** *** *** ***
我们没想到那时会有人找来,更没想到来的是野妞的父母和我的爸妈,后来我们才知道,猪皮和甲鸟回去之后找到我们的家长,说野妞勾引我在高渠苟合,因为我的年龄和身体都小,两家都把这事怪到野妞头上,但两家都不敢声张,猪皮、甲鸟和粘鼠更是不敢声张,这事便在悄无声息中过去。
野妞的父母觉得愧对我的爸妈,我爸妈也不肯原谅野妞,两家的关系变得生陌,直至四个月后,野妞的肚子大起来,她的父母迫于形势,逼她嫁给本村的四十岁的光棍李贵。
我被爸妈丢到县城的舅舅家读书,三年来不准回家,我舅也从不向我说我家的事情,因此对野妞的命运一概不知。初中毕业后,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县城重点高中,高一结束的那个暑假,爸妈方肯领我回家,其时我已经十七岁,生得只有一百七十三公分,虽然不是很高大,但比当年的猪皮、甲鸟都高壮。
野妞在四年后再次见到我的时候,她愣是傻笑,笑了很久,笑得眼泪稀哩地流,她身旁的美丽小女孩扯着她的衣袖,说:「妈妈,你又哭了。」「你变了!」我不敢跟她多说,急急忙忙地逃开,她在我背后大哭,她的女儿也跟着哭。
我不敢问爸妈有关她的事情,但是奇怪她为何会住在娘家,于是通过一些旁言,我了解到李贵在她的女儿出生后的第九个月,不知怎么的,和猪皮厮打,被猪皮捞起石块砸碎脑袋,结果猪皮最终没有用石头砸破我的头,反而被一颗小小的子弹崩开了他的脑壳。
李贵死了,他光棍一条,没亲没故,野妞带着九个月的女儿回到娘家……*** *** *** ***回家后的第六天,野妞的父母来找我,我不知道他们的来意,但感无脸面对他们,或者他们也同样感到无脸面对我,他的父亲不停地抽着水烟,她的母亲也不言不语,我只得问他们找我有什么事,她的母亲忽然朝我下跪,哭着说对不起我,她的父亲吐出一口浓烟,说:「你陪陪野妞吧……她苦,常流泪,自从你回来,她没日没夜地哭,动不动就揪打女儿,是我们对不起你们,我们有罪啊!」正感不知所措,我爸妈出现在门前,爸说:「你也长大了……你喜欢,就去吧。」……我冲进野妞的房,看见她坐在床沿,抚摸熟睡的女儿,并不像她父母所说的暴力,而是满怀母性的温柔。
她看见我,流了一会泪,哽咽:「你来了?」
「我来了。」我说。我把门反锁了。
「我以为你不要姐姐了。」她说。她哭,她也笑。
她解衣。两颗乳房露出,也露出了她满身的伤痕,看得我心酸。
乳房比四年前大很多,像木瓜,比木瓜圆,但没有垂吊,它们耸挺。
我双手托她的肉,弯腰含她的奶,她抱着我的头,说你要吃奶不,弄大姐姐的肚子,姐姐天天喂你奶吃。我说我要吃你。我双手扒脱掉她的裤,她张着腿,一双小腿儿吊在床前,黑浓的阴毛把她的阴户遮盖。我说你浓了,她说久未被人耕种的地,自然生满野草。
她又说让我瞧瞧你的锄柄……
我站直身体,解开裤头,肉屌跳出,她双手紧握我的屌,说,我的山浩果然没辜负姐姐的期望,生得一根好屌,又粗又长,红通通的像要喷血……她张嘴把我的屌吞吮,我愣然片刻,双手抓住她的豪乳揉搓,眼睛却看着她的脸庞,其实她并没有变多少,只是比以前多了妇女的神韵,也许因为劳作,她脸上的肌肤透着红黑,略见粗糙,但那秀美的脸蛋依然保持当年的丰姿,我这时想起,她今年二十岁,而我之前把她当成妇女——二十岁,不就是一个青春少女么?
长期包裹在粗布里的肌肤洁白滑嫩,只是小腹有一些隆胀,但仍然结实和弹性,只是她的手掌,已经没有当年的细腻,握在我的肉屌上,她的手掌显得些许的粗糙、些许的过大……我没能够坚持多久,大概两分钟,急急地射精进她的嘴,她把精液吞了,仰脸朝我笑,说浓浓的热精她好喜欢,我埋首吻她的嘴,同样地品尝到我的精液的味道。
激吻后,她说,山浩,你吻吻姐姐的穴,姐姐曾干净十六年,被三个畜生弄脏,姐姐现在也干净了三年,但姐姐喜欢你再次把它弄脏,永远地把它弄脏……我跪在床前,扒开她的腿,双手拔开她黑浓的毛,看见她的屄,熟悉而又陌生,她本来洁白的阴唇变得有些深色,我记得以前她的阴唇也没有这么肥大,但现在肥隆起来,那道肉缝也稍稍地翻张,只有小阴唇依然桃红,由小阴唇组成的洞也比以前大了些,淫水从她的洞流出,湿红的小阴唇像被雨淋过的桃肉。
「山浩,是不是比以前难看?我生了孩子,缝了好几针……」我的脸钻进她的胯,咬住她的肉,她呻吟一声,没有继续说。
因为没洗澡的缘故,她的屄有点汗骚味,但不知道怎的,我喜欢这味儿,口舌捣着她的嫩肉,不停吮吸她的骚水。我的肉屌再次勃硬,她抱着我的头,说山浩插姐姐,山浩快插姐姐!
我扛起她的比以前粗圆的腿,发觉她的屁股比以前圆大、比以前更有肉感,我学着以前的样子,把肉屌抵插她的肉缝,努力了几下,未能进入,她咯咯地笑了,伸手抓住我的肉屌,往她的肉洞塞,整个龟头被她塞进肉穴,跟以前一样的紧,但这次我没有流血,她也没有。
她说我的肉屌让她好舒服,要我狠狠往里插,我使劲地沈腰刺插,肉屌整根插入她的肉洞,胀得她的大阴唇高高折隆,难以说出的舒服包围我的屌,人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插进女人的肉里的美好。
「山浩真好!山浩真强壮,山浩满足姐姐哩……」她哭,眼泪流得比骚水急。
「——你以前不是说,我插你的时候,你都不哭吗?」她说不哭,她喜欢;后来她又说,山浩插姐姐,姐姐就哭,天天给山浩哭,因为喜欢。
我说野妞,你的伤是谁打的。她说一个死鬼打的,她不从他,他揪着她在床打、绑着她打,打了又插、插了又打,她希望能够把肚里的野种打掉,可是野种没打掉,他倒被别人打死。我知道她说的死鬼是光棍李贵,不知该说什么,只是摸着她的伤痕,想哭,但哭不出。
她的屄水流得浓。我扛着她的腿,压在她的身,卖劲地插着,这次我插得很久,也许是刚射了精的缘故。她被我插得高兴,她说她高兴会流泪,不高兴也会流泪,她说她以前不流泪。
我没有语言,只有动作。我的动作只有一个,只是不停地插;插着她的肉。
她的肉柔软、多汁!我说野妞你松了,她说没松,水多了自然叫山浩插得顺畅。
她又说,你强奸我吧,下次你强奸我,我不给你流水,紧你!
我感动,说野妞都紧,她哭着说山浩也粗大。我喜欢她说我大屌,卖劲的插着。
我的汗水滴落她的身体,和她的汗水融合,她喘着说做完要和我洗鸳鸯浴,忽然推了我一把,翻身趴在床,嚷着狗插狗插山浩我要狗插,扯着我的屌要我做她的狗,我于是真做了她的公狗,但公狗不好做,我抓着她的奶水咬着她的背,没多少下就软了,屌吐白沫地趴在她的背上喘风。
她软在床,旁边躺着她的女儿。她伸手扯掉女儿的小裤,我看见她女儿的小缝,红嫩红嫩的可爱。她指着女儿的细缝,说山浩舔舔。我惊了,我不干。
她哭了,重复地要我吻她的女儿。我就看着女孩的小器,心里有种变态的冲动。我舔了,舔着女孩的嫩。
「什么感觉?」她问,我说:「咸。」
她咯咯地笑,「等野种长大,山浩把野种开了。」我惊觉她病态,但看起来不像疯。
此时女孩醒了,女孩哭,她揪起女儿的小白屁股,大巴掌地拍打,我抓住她的手。外面传来她父亲的声音,女孩哭得厉害,她父亲要进来,她扯了被单往身上盖,我裸着身把门打开,她父亲进来抱了她的女儿。他看了看我,朝我竖起个大拇指,啥也不说就出去了。
我回头,问她为何总要打女儿。她笑,笑得像哭。我抱了她。我的屌又硬,插进她的肉,有些干,很紧。
「山浩你可知道,我爹娘和你爸妈初时以为野种是你的,都不准我打。一年前我哥从外地回来,我打野种,他揪着我的头发打我,我把被三个畜生轮奸的事说了,他跑去打甲鸟,打断了甲鸟一条腿,他也蹲牢去了。」难怪我这趟回来没有见到她哥;记得当年发生那事,他哥觉得丢脸,什么都不说,跑到外面谋活事,因此野妞嫁的时候,她哥也不知晓。
说到她哥,她更是哭。她说她葬送了哥哥的幸福,她哥在外地几年,混了个名堂,拿了叠叠钞票回来给爹娘,只是赚到的钞票还没讨个媳妇,就为了她去蹲牢,她心里痛恨!
「过几年会出来。」我安慰她,吻她的汗和泪,也吃她的骚水。
我和她直到做天黑,她说她从未得到过这么多高潮。
吃了晚饭,她洗了澡又过来找我,我爸妈看见也没说什么。我抱了她到我的房,在床上滚到天亮,流了满床的水,但这次没了她的泪,只有汗和骚。
整晚,她不停地重复一句话:你肏我到死,我是你的肉,你肏我到死……*** *** *** ***整个暑假,我和野妞几乎都在床上渡过,这是我们两家的秘密,除了两家的父母,谁都不知道此事。然而不好的事情发生了,野妞的月事没来,在将要开学前的四天,我特意跑到县城给野妞买了验孕试纸,回来往她的尿里一插,她果然怀了我的种。
我把这事跟爸妈说了,爸妈和野妞的父母商量,野妞的父亲说生吧也给山浩生个孩子,不管别人怎么说。我爸妈也同意了,野妞那么喜欢我,是该有个我的孩子。
然而野妞似乎不高兴,我插她的肉的时候,问她不想替我生孩子吗,她说她是寡妇,我说不上学了跟她结婚。她苦笑,还是笑得咯咯地响,咬着我的鼻尖骂我浑,我说我真的娶。
「——我生是你的肉,死是你的魂,你以后有出息娶了媳,你回来看看我,理理我垄上的草。」我抽出肉屌,趴到她的屄,用牙齿梳理她的毛,说我这辈子只理你的草,她不愿意,说男人的耙要多理几块田的草,男人才会更有劲,还说她要把她田里的草理光了逼我去理别的田的草。我取了剪刀和剃胡的刀片,把她的毛剃光。
光洁的屄、隆起的肉、夹露的唇。我一把插了进去,她推开我,拿了工具把我的毛也剃掉,然后咯咯地笑,说进来,光头小弟进姐姐没有草的洞。我插了进去,没了毛的屄垄,像小女孩的肌肤一般嫩滑。
她说明天你陪我到集市吧,这辈子你还没有陪我到集市买过东西。天明我陪她到集市,但她没有买东西送我,买了一包不知名的药和一瓶酒又买了一把短刀和一叠冥钱,我问她为什么,她说我哪天不要她了,她就杀了我,顺便给我烧些纸钱。
虽然我很想相信她说的话是假的,但我的心还是感到寒。
回家和她做爱的时候,老想着她买的那把刀,扎在心里冰寒冰寒的……后天我要到县城上学,我有许多想要跟她说,她却不肯跟我说话,只是跟我死活地做。半夜里,她穿了短裤跑出去,回来时手里拿一瓶花生油,我问她做什么,她说如果不嫌脏,把最后的洞也给我。
我把花生油涂进她的屁眼,艰难地插入她的肛门,在干涩和油粘中,我很快射了精。
斑斑黄白和缕缕鲜血凝结在她油滑的屁眼,忘了擦……*** *** *** ***翌日,我忙碌着上学前的事项,整日没找野妞,也没见她出现,晚上找她的时候,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,问她的父母,他们也是不知。直到晚上九时多,有人冲至她家,说野妞杀人了,野妞杀了甲鸟……我们两家人往甲鸟家奔,十分钟后到达甲鸟的家门,见到门前堵着一堆人,甲鸟的老母哭得猪叫般的惨痛,他的两个兄弟也嚎叫不止。我推开人群,冲至门前,被他的两个兄弟拦住,我挥拳把他们打倒,冲进屋里,看见野妞赤裸地靠坐在床栏,胸前插着她那天买来的刀。
她看见我,还是咯咯地笑。
甲鸟的尸体,胯间一片惨红,他的屌被砍成好几断,丢弃在他的尸体旁……我喝喊:「你疯了?」「我是疯了,我早就疯了!我被三个畜生轮奸,胀了肚子,被逼嫁给光棍,天天被打……我故意跟猪皮偷奸,故意让光棍看到,叫他们狗咬狗,葬了他们的命。」「我今晚拿了酒,酒里掺着老鼠药,跟这拐子说要跟他续前缘,他爬上了我的肉,高兴地插我,高兴地喝了我的酒,我趁着他高兴得晕了,也高兴地取出藏在衣服的刀,高兴地捅他,他高兴地死了,我再高兴地把他的高兴也割去,然后他们来了,我要让他们知道老娘今晚有多高兴,于是高兴地插进自己的胸膛,老娘就是高兴!」「——你真的疯了!」我悲喝着,走向床前。
她甩手把刀抽出,血液喷涌……
我抢过她的刀,她哭,她说你痛吗,你痛的话怎么不见你流血?
血……
我把刀插进自己的大腿,横抱起她,一拐一拐地走出去。
没有人拦我,甲鸟的兄弟也让出了道……
我抱着虚弱的她,走进黑夜,她的父母和我的爸妈跟在后面。
「——山浩,我下辈子不要做野妞,我要做你温柔的姐姐,下辈子你认得我的肉吗?」「野妞的肉,我都认得……」「山浩,姐姐的肉今晚又脏了,以后都不能为你洗干净,但我留了一个干净的肉给你,她没有姓,只有名字,叫芙蓉……那肉虽然来得肮脏,但她本身很干净,你替我照顾好她,因为她也是姐姐的肉。」「嗯,我会照顾好芙蓉……」「山浩,姐姐还有个好恨的人,姐姐恨不得吃他的肉,可是他的肉是世界上最脏的,姐姐啃不下,你长大后找到他,看看他有没有女儿,然后你像他当年对待我一样,也把她的女儿糟蹋。」我没有说话,她逼着我回答,我只得点点头,在黑夜里,也不知道她是否看得清楚?
她说话的力气越来越弱,但是她似乎还有说不完的话要对我说,我只能够听着,什么话都说不上。
「山浩,我这辈子被葬了,同时我也葬了很多人。我葬了你的童真、葬了父母的脸面、葬了孩子的人生!但我,葬你在我的心里,从你说我哭的那刻起,姐姐就葬你在心里,葬得很深,谁都挖不起。」「我不知道你被我葬得可高兴,可是姐姐知道明天会被你亲手埋葬,姐姐真的好高兴!能够给山浩葬,是姐姐最幸福的时刻,所以姐姐提前买了纸钱,让山浩一路地撒,也让纸钱擦干姐姐一路的眼泪,因为姐姐怕太高兴,流太多的泪!
山浩,你叫一声姐姐,你一直都没叫过……」
「姐。」我哭。
「别哭!山浩,姐姐给你唱首歌儿,姐姐今晚高兴,把藏在心里四年的歌儿唱给你听:
小小的鸟儿,跳啊跳
跳上了竹叶梢;
轻轻的风儿,摇啊摇
摇落了一地愁。
摇啊摇,女儿笑!
笑落泪水,满地浇。
葬我的眼泪,
在你心里头……」
*** *** *** ***
【完】